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认为,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娱乐的能力?

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认为,分析的终极目标是让患者具有爱、工作、娱乐的能力。爱和工作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但为什么他会特意强调“娱乐”?
在当前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中,花在娱乐上的时间似乎会很容易地被认为“被浪费掉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如何看待“娱乐”,看待这些被“浪费”掉的时间,看待进行着娱乐和浪费着时间的我们自身?这正是这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部分。
文/马尔科姆·阿迈尔
本文摘自《时间》
图/DAVID EGAN
巴斯蒂安经常玩电子游戏。尽管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没有生活”的人,然而他还是喜爱在一个比真实的生活环境更稳定、丰富又多样化的世界里消耗时间。
在游戏的过程中,他花费精力,也与别人合作,沉浸在比其他时刻更令人兴奋的感觉中。他也玩纸牌或者桌游,还喜欢看电影,但所有这些比起复杂的游戏世界——在那里他指挥着游戏中的人物,和十几个扮演幽灵、仙女或怪兽的玩家一起占领城池——好像都没什么意思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娱乐看作一种消遣,好让我们的精神有一种懒散(passif)的时刻,从紧张中解脱出来,在努力后得到休息。
然而,在娱乐中,我真的是懒散的吗?打牌动员了我的注意力、记忆力,还得知道规则。通过游戏,塞巴斯蒂安发展了他的想象力、严谨度、技术能力、战斗力,还有审慎。
看起来,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动用并发展了我们自身的智力或者体能,知识甚或我们视作美德的品质——比如耐心、决心。如果说人们从积极性中期待的是一种我们可以施展力量和品质的状态,那么沉浸在娱乐时光中的我是活跃(actif)的。
但为什么当我玩的时候,别人总想把我拉回正轨,说我在浪费时间?
说我在玩的时候是懒散的,是将被视作活跃的工作或学习时间与娱乐时间对立起来了。然而,当塞巴斯蒂安的父亲对他说:“你玩游戏是浪费时间,积极一点,来做作业。”他事实上抱有一种对活跃的片面理解。
对他父亲来说,处于活跃状态意味着投入到一段有用的时间中去,这暗示着他把工作的有用时间和消遣的无用时间对立起来了。
但消遣真的无用吗?我们已经看到了娱乐可以调动我们的各种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娱乐的个体是有用的,能帮助他学习和耗费精力。那么娱乐到底对谁没用呢?
游戏,休闲活动,当它们成为工作或学习中的停歇时,是一种娱乐。娱乐是暂时的,是任务的补充。因此,每一项所谓无价值的活动都有一个目标:我休假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我周末看电视是为了调剂一周的学习,我玩游戏是为了以一种更放松的状态去做作业。
那些我所认为的空闲时间,实际上是从社会层面而言有用的时间。正因为我被允许娱乐,我才接受把我的剩余时间投入到艰难的工作中去,也因此不否认围绕着工作进行的社会指令,尽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限制。
因此我们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娱乐尽管独自进行,但对社会是有用的。当一个玩家对电玩“上瘾”的时候,例如塞巴斯蒂安,他不再去做艰难的工作,只顾玩那些原本是为了使他更好地支持和接受工作的游戏。这时候,他的娱乐活动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无用的,因为它危害了他的学习和工作。
说我娱乐是浪费时间,说娱乐无用,就是在说我浪费了对社会来说珍贵的时间。社会要求我工作,要求我投入到它分配给我的任务中,要求我不反抗维持它的必要秩序。
批评塞巴斯蒂安将虚拟生活置于他的日常生活之上,这是父亲针对儿子对秩序的抵抗,所给出的社会性评价。说到底,他批评儿子的是他逃避了一种被称为社会现实的现实,在生活中过了一段被社会现实合理地定义为“虚度”了的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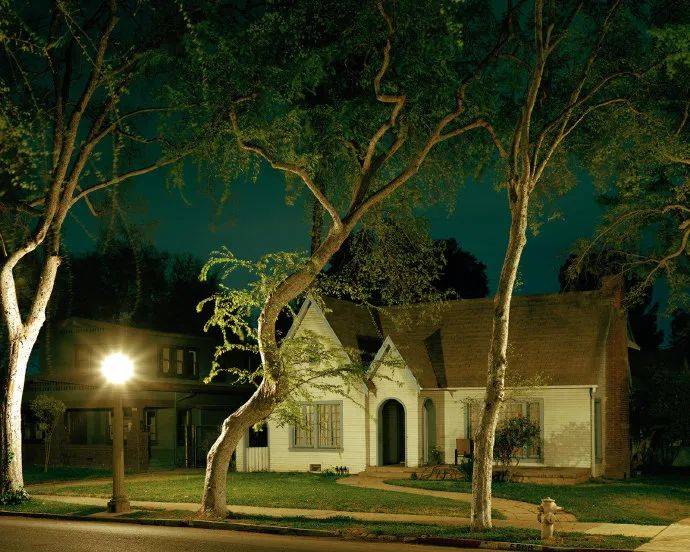
从词源学上讲,娱乐(se divertir)意味着“从······转开”,“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上”。如果不被重视的问题是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什么之上(vers quoi)(转移到电子游戏、一场音乐会或一局牌上没什么不同),那么相反的,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娱乐的时候我们从何处(de quoi)转开了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从一项工作、一种日常,或者一个有压力的现实那里转开了注意力。娱乐经常被当作一段愉快的时光来度过,我们倾向于将它和学习或工作的艰难时刻对立起来。但归根到底,为什么工作时间不能是一段愉快的时光呢?甚至那些喜欢上课的人也想要娱乐。这种愿望有时显然是一种需要。
娱乐的趣味是一种很特别的愉悦,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们有时好像急于逃避现实吗?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举了打猎的例子,告诉我们花一整天追逐野兔的人们“不会想要别人拱手相送的猎物”。但为什么要打猎呢?如果说猎人的目标并不是抓住野兔,那又是什么?
帕斯卡尔说,事实上,猎人的真实目标不是抓住野兔(这会被看作有用的时间),也不是这项活动给他带来的乐趣(这会被看作愉快的时光)。
他的目标,首先是逃避他难以面对的某种现实。更确切地说,人需要娱乐,为的是摆脱对自身悲苦的自知,这与人的有限性(finitude)相关——也就是说,对必定到来的死亡的自知。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猎人而言,重要的不是抓住野免。帕斯卡尔说:“这只野兔并不能保证我们避免对死亡和悲苦的视线,然而打猎——它转移了我们的视线——却可以保证。”
娱乐的时间,简单来说是分散注意力的时间(temps de la diversion),我通过做看起来轻松的事情,试图逃避的是我自己,以及我作为人的境况。
娱乐的人逃避的也不是日常的无聊或失望,这是帕斯卡尔通过国王的例子指出的。“国王周围的人只想着取悦他,不让他去思考自己。因为尽管他是国王,但假如他想到自己,他也会痛苦。······没有娱乐的国王是一个满心悲苦的人。”因为即使他是国王,即使他能通过权力占有各类财产,他也一样会死。“如果他没有我们所谓的娱乐,就是一个不幸的人,比他最微不足道的、可以玩乐的臣民还要不幸。”
因此,透过所有虚假的目标,在娱乐中(我在网上做个小测试提高积分,我打猎捉到野兔,我休息一下看部电影),人,无论是谁,都只是想要忘掉他会死亡的这个念头——顺便一提,人也在看似最严肃的活动中寻求这个目标。由此得出,娱乐有时带着必要的强制性力量强加在我们身上。
帕斯卡尔又说:“监狱是最可怕的折磨。”因为那里完全没有娱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直面自己。
因此娱乐并不应该遭受指责,帕斯卡尔说:指责一项证明我们自身悲苦的活动,只会导致对人类本质的错误认识。娱乐者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为了活动而活动——因为活动让他远离烦恼——且认为他在娱乐中所追随的目标使他幸福。
但帕斯卡尔补充道,认为娱乐会让我们歇下来因而不去娱乐,这种想法也是徒劳的。因为拒绝娱乐是不近人情的,“以此为基础的哲学家们,认为世界是不理性的,花一整天追逐野兔而不想买一只的行为是不理性的,这些人基本上不认识我们的天性”。
不想娱乐的人是“笨蛋”,帕斯卡尔说,他所忽视的是“他终究只是一个人,也就是说,能做很少或很多,无所不能或一无是处”。
即使不停地增加自己的活动,让自己“很忙”,人也无法逃脱自己的境况。因此,人类要么拒绝注视自己,甚至去选择“一切猛烈的、狂热的活动,好让自己不去思考自身”,要么接受直面自己生命有限的宿命,冒险投入到无尽的焦虑中。但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贺拉斯说,“活在当下”(carpe diem)——“抓住今天,尽量不要相信未来”——这句话源自伊壁鸠鲁学派的伦理信条,恰恰正在帮助我们摆脱选择的困局。
在死亡与生命相对立的这一范畴内,为什么要担忧呢?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逃避呢?源自对死亡意识的焦虑,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开,是我们获得幸福的首要障碍之一。
想象死亡,想象地狱的存在和上帝的审判,对于伊壁鸠鲁来说,就是维持一种幻觉。这种幻觉阻止我们去寻找幸福和快乐,但它在此时此地却是正当的、可能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迷失在丰富的娱乐活动中而不关注自身,相反,应该转向自己,面对自身的恐惧,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
面对死亡,首先是去思考死亡是什么。然而,伊壁鸠鲁说,对于活着的我们而言,“死亡什么也不是”。我们永远不会遇见死亡,我们永远不会与它有任何联系,因为很显然,活着就不是死去,死了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因此,应该相信幸福是可以获得的,否则我们很可能做任何事情,只为得到幸福,而这会促使我们追随一些虚幻的价值观和利益。
事实上,追寻不切实际的利益才是浪费时间。
如果停止分割时间,停止把它分散到各类活动、任务和游戏中去,以此避免直视我们的本质——活着且终将死去——那么面对一去不返的时间,我们将不那么胆怯。
说到底,空闲时间并不是娱乐的时间,娱乐时间与艰难的工作相关联,使我们能够忍受它或者让我们暂时忘掉人的悲苦。
空闲时间是伊壁鸠鲁定义的自由人的时间,也就是说,不畏死亡、直面死亡的人的时间。如果我们决定当下就是对的时刻(la bonne heure),我们追寻的利益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而不存在于外物,那快乐和宁静二者皆可获得。
我们将为人类自身创造出一种时间,短暂却自由。
| 推荐咨询师 | ||
 晓晖 |
||






